|
原标题:“小书”说“大事”(新书创作谈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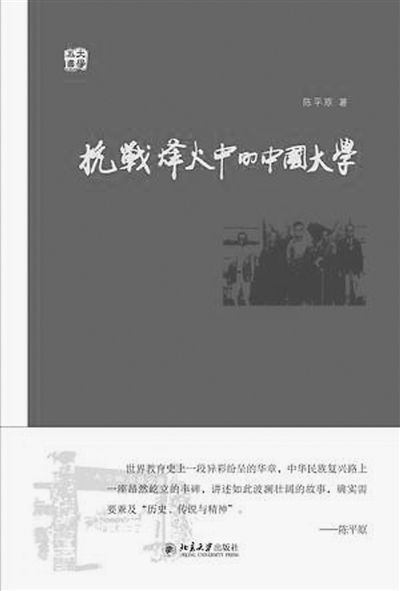 |
|
《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:陈平原著;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|
写完题为《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》的“绪言”,结尾处,我添了句:“仅以此小书,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”别人以为是例行公事,或故作“谦虚状”,在我却是很认真的。因为,我对此书的定位是:一本沉甸甸的小书。说“小书”,指的是篇幅;说“沉甸甸”,则关乎论述对象。
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,容易说的,是有形的,如培养人才、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;不太好说的,是无形的,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。具体说来,硝烟弥漫中,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,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。抗战中,大批中国大学内迁,其意义怎么估量也不过分——保存学术实力、赓续文化命脉、培养急需人才、开拓内陆空间,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。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,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、“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”的西南联大等高校,也算是“别有幽怀”。
类似的话,我在书中多有表述。如此兼及政治史、教育史与知识分子心态史,可说的事情、可发的感慨、可写的文章实在太多了。可最后,我选择了以“小书”来说“大事”。我希望透过历史资料的发掘、生活细节的勾勒、教育规律的总结、读书人心境与情怀的凸显、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的引入,把中国的大学故事讲给世界听。“基于此目标,第一,删繁就简,去掉原本收入的两篇长文,使其显得一气呵成;第二,兼及雅俗,是历史著作,但希望具备可读性;第三,面对这段本就很感人的历史,不做过分渲染,保持平静与客观—— ‘煽情’不是本书的工作目标。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准确地描述那一种历史情景,理解并阐释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,至于判断,让读者自己下。”这是我关于本书写作策略的说明,有自我辩解的成分,但不全然是。
之所以说“大事”而采用“小书”形式,借用清人郑板桥的说法,“删繁就简”的目的是为了“领异标新”。并非偷懒,也不是力所不逮,而是希望在今年刊行的众多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图书中,能有“自家面目”。舍弃面面俱到或鸿篇巨著的追求,选择兼及学界与大众的写作策略,乃是基于我对“小书”的怀念。
9年前,我就撰写过一篇《怀念“小书”》,感叹“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,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?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‘小而可贵’的书,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?”谈过了管理体制、制作方式、接受途径等,我还反省学者“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”。在我看来,此类“小书”,若真想达到“小而可贵”的目标,必须是识大体,讲趣味,思路清晰,论述准确,不卖弄学问,也不逞才使气。说实话,无论大书小书,能给读者留下三两个值得认真琢磨的话题,或五六句过目不忘的隽语,这就够了。
除了文字不多,篇幅上自我限制,再就是笔调。虽是小书,亦恪守史家笔法,有一说一,有二说二,不夸饰,不煽情——即便谈及教授们危难之际的“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,也取澹定姿态,极少使用形容词。我相信,事件与人物本身就很精彩,加上多年的沉淀与发酵,只需稍稍提示,读者自能心领神会。在这个意义上,作者根本用不着“夸夸其谈”。这真应了鲁迅那句话:“只因写实,转成新鲜”。
讲述70年前的故事,仅仅“激动人心”是不够的,还需要大的历史视野,以及冷静的思考和深入的阐释。这样,才有可能超越“纪念图书”旋起旋落的通病。虽是“小书”,希望真的能“沉甸甸”,不仅今日可读,十年二十年后,也还能经得起读者的挑剔与审视。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5年08月18日 24 版)
[责任编辑:武新梅]
|